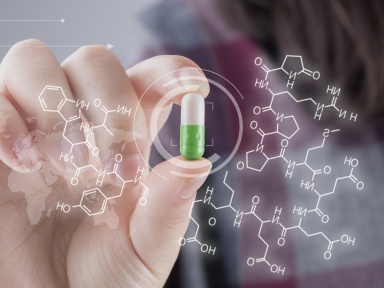
近年来,老药新用的研究策略已成为药物研发的热点。许多临床上正用于疾病治疗的药物,以及曾经或正处于临床前或临床试验中的候选药物,被重新开发,应用于新的适应症的治疗。根据老药新用发现的技术特点,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临床治疗特定疾病为目标,结合多种方法,从临床应用的药物中发现针对特定疾病具有治疗作用的药物,发现现有药物的新用途;二是应用现代新药发现的先进技术方法,包括高通量、高内涵药物筛选技术、药物设计和虚拟筛选技术、靶点对接筛选技术等,从已经上市的药物中发现新的作用机制,定位新的用途,研发新的药物。
基于老药新用的需求,对疾病的认识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临床症状,二是病理机制。药物治疗通常分为对症治疗和对因治疗。其中对症治疗主要通过临床症状来评价药物的作用。它虽然不是疾病的根源,却是疾病重要的表现形式。因此,不能解决临床症状就无法证明治疗效果。而临床上发现新的药物作用往往也都是通过有效地改善了症状发现的。这也证明了深入认识疾病的症状表现及其对疾病预后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对因治疗的理论基础则是明确了疾病的病理机制。只有深入认识疾病发生发展的机制,才能找到合适的药物并从根本上治疗。因此,病因更是成功治疗疾病所需要把握的关键因素。从不同角度入手是对因治疗和对症治疗的区别,不过这两者并没有正确与否或轻重之分。因为病因或症状是辨证关系,只有深入认识疾病病因,才能够更加高效地找到合适的药物。如在抗击 COVID-19 的过程中,抗病毒药物应用尤其突出。从病因分析,感染是由病毒引起,因此抗病毒药物治疗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由于早期对 COVID-19 的病理过程认识不足,现有临床抗病毒药物并没有获得理想的效果。因此,老药新用的研究需要坚实的科学支撑。其中急需包括对药物和疾病全面而深入的认识,才能够保证老药新用的准确和成功。
老药新用研究策略
①基于已知作用机制的老药新用
已上市的药物一般已明确其基本作用机制。例如,作用于神经系统疾病的药物,围绕其对原有适应证的作用机制,在临床上可能有多种适应证的选择,基于已知机制探索新适应证,也成为老药新用的重要模式。依达拉奉是一种抗脑缺血药物,最早由日本田边三菱制药公司研制,并于2001 年在日本批准上市,最初主要用于治疗急性脑缺血。依达拉奉的主要作用机制是清除自由基,发挥抗氧化作用,表现出明显的神经保护作用,达到治疗脑卒中的效果。在依达拉奉神经保护作用的基础上,人们认识到有一种严重危害患者生命的神经系统疾病—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ALS),其病理过程与神经氧化损伤密切相关。经过十余年的研究,2015年,依达拉奉首先在日本获得批准用于治疗 ALS,2017年也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批准,我国也于2019 年批准该药用于治疗ALS。依达拉奉成为基于机制实现老药新用的成功实例之一。
阿兹夫定属于核苷类似物,其并非是针对SARS-CoV-2 所研发的抗病毒药物,而是有着漫长的历史。其最早是用于治疗丙型肝炎和艾滋病,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口服小分子抗病毒药物。COVID-19疫情暴发后,经研究发现 SARS-CoV-2 和艾滋病毒同属于核糖核酸(RNA)病毒,阿兹夫定能抑制SARS-CoV-2的复制。故在2022年7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附条件批准阿兹夫定片(规格1mg/片)上市,用于治疗中型COVID-19 的成年患者。
②基于新作用机制的老药新用
对上市药物进行重新筛选并发现新机制,是老药新用的另一重要途径。沙利度胺于20世纪 50年代合成并被证明具有镇静作用,曾用于缓解妊娠反应,但其不良反应导致近万名畸形儿出生。尽管沙利度胺于1961年撤市,但在随后的50年中,不同团队对其药理学作用持续研究,发现了多种新机制。1965 年,研究发现沙利度胺可治疗麻风结节性红斑,并具有免疫调节特性,如调控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的产生、调节淋巴细胞亚群平衡及抗血管生成作用。1998年,FDA 批准沙利度胺用于治疗麻风性红斑结节病。1994年,研究发现沙利度胺可抑制新生血管生成,而实体瘤的生长依赖血管生成。2006 年,FDA 批准其联合地塞米松治疗初诊骨髓瘤。通过新机制研究,沙利度胺作用于新适应证,成为药物再定位的典型代表。
二甲 双胍是“老药新用”的一个典型代表。二甲 双胍属胍类衍生物,主要适应证为 2型糖尿病。近来,随着人们对二甲 双胍作用机制及生物活性的深入研究,发现其具有潜在抗癌作用。二甲 双胍对乳腺癌、卵巢癌、胰腺癌、肺癌等恶性肿瘤均有抑制作用,其主要机制包括:AMP 活化蛋白激酶通路调控、改善铂类耐药性、抑制癌细胞转移、调节免疫细胞功能及增强治疗敏感性等。
伊曲康唑是一种广谱抗真菌药物。在筛选抗肿瘤药物的过程中,研究者们发现伊曲康唑具有拮抗多种内皮生长因子、阻断Hedgehog 信号通路、抑制胆固醇转运的能力,并最终产生抗血管生成的效应。研究表明,伊曲康唑能够诱导血管内皮 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表达的沉默,以剂量依赖的方式抑制内皮细胞增殖和血管形成,从而抑制乳腺癌的生长。
③基于药物副作用的老药新用
药物副作用是由药物的本来应用目的决定的。利用药物副作用的产生机制,可将药物应用于新适应证或治疗目的。依据药物的作用、副作用和病理机制,合理使用药物,方可充分发挥作用,达到最佳治疗效果。阿司匹林已有120多年临床应用历史,早期作为解热、镇痛、抗炎药物用于治疗关节炎、慢性炎症及感冒发热,是常用药物。长期应用中发现,阿司匹林可导致凝血障碍。研究证实,不同剂量阿司匹林均具有抑制血小板聚集作用。基于阿司匹林抑制凝血的特点,开发其抑制血栓形成、预防心肌梗死的新适应证,并在临床上普遍使用。
中药现代研究中的老药新用与新药研发
中药的老药新用研究采用大量现代技术及药物研发路径,成为新药研发的重要途径。针对中药的现代药学研究已获得一批能有效治疗疾病且安全性高的理想药物。长期的临床应用为中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为药物作用机制研究提供了资料支撑。通过应用符合药物评价实际的技术方法(如真实世界评价方法),以及技术方法的创新,可获得更多有价值的数据,对中药现代研究和创新发展发挥积极促进作用。COVID-19疫情发生以来,已有大量传统中药以老药新用的方式用于治疗新型冠状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SARS-CoV-2)感染。中药的老药新用通常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针对新疾病治疗使用已有药物的探索和尝试;二是对临床药物进行新用途的认识和开发。例如,临床常用的注射用丹参多酚酸对脑缺血的治疗作用,是对丹参临床用途的再定位;20世纪中期研发的麻黄素滴鼻液治疗鼻炎等多种疾病引起的鼻塞,也是对麻黄临床应用的再定位。对中成药的再定位研究也很多,发现了中药更多的新用途,并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
老药新用是一种研究的模式或策略,其内涵包括复杂的科学问题,而作为一种研究模式或策略,可以在新药研发中更广泛地应用。比如在抗新冠病毒感染过程中,治疗药物研究不仅仅局限于上市药物,一些处于研发阶段的药物也被引入到临床研究中,成为老药新用研究范围的扩展。例如,在2020 年初针对瑞德西韦抗 COVID-19 进行的临床研究,就是老药新用扩展到未上市药物的实例。新药研发的过程是对候选药物进行物质和药理成药性的评价过程。根据国家药物管理的要求,一个新药的研发大致需要通过药物发现、临床前研究、临床研究三个阶段,而每个阶段都对应着巨大的投入。而从已经上市的药物开发出一个新药,其过程与全新药物的开发相比,可以简化很多重要的过程,不仅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而且可以大幅缩减研究力量和费用。从研究一个新药品种的目标出发,由于已上市药物的物质研究和安全性研究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而且有了临床应用的基础,可以省略很多研究过程。如物质基础相关的生产工艺和标准,原料药与稳定性,以及药物的药动学过程以及安全性等药理学内容,都不会因为适应证的不同而产生巨大变化,可以省略研究过程,极大缩短药物研发的时间。
参考资料:
[1]杜立达,张雯,宋俊科,等.老药新用研究策略与应用(1)——基于临床治疗需求的老药新用研究[J].医药导报,2023,42(02):150-154.
[2]杜立达,范晓诺,宋俊科,等.老药新用研究策略与应用(2)——基于新适应证发现的研究策略与应用[J].医药导报,2023,42(03):299-303.
[3]谭辰,徐张润,薛阳,等.老药新用在乳腺癌治疗中的研究进展[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医学版),2024,44(11):1454-1459.
[4]周宇恒,李玥潼,王越,等.基于老药新用二甲 双胍抑制卵巢癌机制的研究进展[J].南通大学学报(医学版),2024,44(02):172-176.
[5]王延学,马可,夏志洁.老药新用之阿兹夫定[J].中国合理用药探索,2023,20(06):25-27.
作者简介:小泥沙,食品科技工作者,食品科学硕士,现就职于国内某大型药物研发公司,从事营养食品的开发与研究。



合作咨询
![]() 肖女士
肖女士
![]() 021-33392297
021-33392297
![]() Kelly.Xiao@imsinoexpo.com
Kelly.Xiao@imsinoexpo.com
 2006-2025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版权所有(保留一切权利)
沪ICP备05034851号-57
2006-2025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版权所有(保留一切权利)
沪ICP备05034851号-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