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3日,中国创新药企百济神州宣布终止其抗TIGIT抗体欧司珀利单抗(BGB-A1217)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3期临床试验AdvanTIG-302。这一决定基于独立数据监查委员会(IDMC)的无效性分析结果:研究难以达到总生存期(OS)这一主要终点。尽管未发现新的安全性风险,但这一项目仍以累计投入超20.9亿元、入组2000余例患者的代价宣告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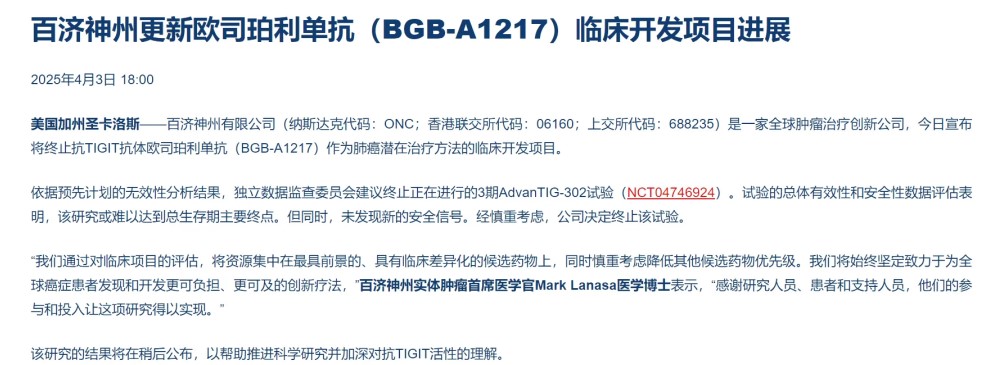
TIGIT曾被誉为“下一个PD-1”,如今却因临床试验接连失败陷入集体性迷茫,这场耗资数百亿美元的研发马拉松,究竟暴露了哪些问题?
烧了20亿,明星药咋就凉了?
作为百济神州管线中的明星项目,欧司珀利单抗一度承载着突破肺癌治疗瓶颈的厚望。AdvanTIG-302试验的设计堪称雄心勃勃:通过将欧司珀利单抗与自家PD-1抑制剂替雷利珠单抗(Tevimbra)联用,直接挑战默沙东的Keytruda(帕博利珠单抗)在PD-L1高表达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的霸主地位。这一策略的逻辑看似完美——TIGIT与PD-1分别作用于免疫系统的不同环节,双管齐下本应产生协同效应。然而现实却给了理想一记重击。中期分析显示,联合疗法在延长患者总生存期上不仅未能超越Keytruda,甚至可能劣于对照组。这迫使百济神州在累计投入20.9亿元后选择止损,而这一数字尚未计入诺华2021年支付的3亿美元首付款。当年诺华重金押注的豪赌,最终因“风险收益比不理想”于2023年提前退场,如今看来更像是一次精准的风险预判。
这场败局背后,是肿瘤免疫疗法研发的典型困境。即便坐拥替雷利珠单抗这一年销28亿美元的PD-1王牌,百济仍难以复刻PD-1单药的成功路径。当Keytruda、Opdivo等药物将PD-1/PD-L1抑制剂的单药疗效逼近天花板后,行业普遍将突破希望寄托于联合疗法。但问题在于,疗效的叠加往往伴随毒性的指数级增长。欧司珀利单抗虽未出现新的安全信号,但其与替雷利珠单抗联用时的3级以上不良反应发生率高达52%,远超Keytruda单药的17%。这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窘境,让联合疗法的临床价值变得愈发微妙。
TIGIT靶点:一场集体幻觉?
TIGIT靶点发现于2009年的免疫检查点蛋白,曾因双重机制被视为“天选之子”:既能抑制杀伤性T细胞的活性,又能增强调节性T细胞(Tregs)的免疫抑制作用。理论上,阻断TIGIT可以同时解除两道免疫刹车,释放更强大的抗肿瘤效应。然而正是这种机制复杂性,埋下了今日困局的伏笔。
早期临床数据就敲响了警钟。无论是罗氏的Tiragolumab、默沙东的Vibostolimab,还是百济的欧司珀利单抗,单药治疗的客观缓解率(ORR)普遍不足15%,远低于PD-1抑制剂20%-40%的水平。这迫使药企转向联合疗法,但疗效与毒性的平衡难题随即浮现。以罗氏2024年失败的SKYSCRAPER-01试验为例,Tiragolumab联合PD-L1抑制剂阿替利珠单抗虽将ORR从对照组的38%提升至55%,但患者总生存期却未显示统计学差异。更讽刺的是,联合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反而比对照组缩短了0.8个月。此类矛盾数据提示,TIGIT可能在某些患者亚群中起反作用——比如通过过度激活免疫系统导致耗竭,或意外增强Tregs的免疫抑制功能。
全球药企为此付出的代价堪称惨烈。过去四年间,TIGIT领域累计烧掉超过200亿美元研发资金,但进入Ⅲ期的药物仅存2款,40%项目已终止。罗氏在肺癌领域连折三阵后,仅剩肝癌适应症苦苦支撑;默沙东的Vibostolimab因疗效不足提前终止Ⅲ期试验;吉利德与Arcus合作的Domvanalimab在非小细胞肺癌失利后,转战消化道肿瘤也前景未明。这场集体溃败不仅动摇了资本市场的信心,更暴露出肿瘤免疫疗法研发的系统性风险——临床前模型的预测性与人体试验结果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
肿瘤免疫疗法的生死劫
TIGIT靶点的困境,本质上是整个肿瘤免疫疗法领域的缩影。自PD-1/PD-L1抑制剂开启癌症治疗新时代以来,行业始终在重复一个魔咒:每一个“下一个PD-1”的豪言,最终都沦为资本狂欢后的泡沫。从CTLA-4、LAG-3到TIM-3,热门靶点的更迭速度越来越快,但临床转化成功率却持续走低。据统计,肿瘤免疫疗法的临床成功率仅为5.3%,远低于行业平均的10.4%。
这种反差背后,是科学探索与商业逻辑的激烈碰撞。PD-1/PD-L1抑制剂创造的商业神话——Keytruda年销售额突破250亿美元,Opdivo、Tecentriq等产品紧随其后——催生了“靶点内卷”的畸形生态。当跨国药企的专利悬崖逼近,寻找“接班产品”的压力迫使行业将资源疯狂投向少数明星靶点。TIGIT正是这种焦虑的产物:顶峰时期全球同时推进的临床试验超过60项,但其中80%集中在肺癌、肝癌等成熟赛道,真正探索创新适应症的研究不足10%。这种“扎堆内耗”不仅造成资源浪费,更阻碍了对靶点机制的深度理解。
百济神州首席医学官Mark Lanasa在宣布终止试验时坦言:“我们必须学会区分科学上的可能性和临床上的可行性。”这句话直指行业痛点——当资本裹挟科学,当KPI绑架创新,原本需要十年磨一剑的基础研究被压缩成急功近利的“流水线作业”。以TIGIT为例,其作用机制至今仍存在争议:究竟是独立信号通路,还是PD-1的辅助调节器?在不同肿瘤微环境中是否具有功能异质性?这些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解答,上百项临床试验就已仓促上马。这种“蒙眼狂奔”的研发模式,注定要付出高昂学费。
我们又能从中吸取什么?
百济神州的TIGIT挫败,对中国创新药企具有特殊警示意义。作为最早布局该靶点的国内企业之一,百济曾凭借欧司珀利单抗的授权交易站上国际舞台,但最终仍难逃“跟风式创新”的陷阱。当前国内仍有康方生物、君实生物等十余家药企布局TIGIT,但90%以上的项目集中在肺癌、食管癌等红海领域,且临床设计高度同质化,这种“扎堆内卷”不仅消耗宝贵资源,更凸显出原始创新能力的匮乏。 同时,百济在终止欧司珀利单抗后,迅速将资源转向BCL-2抑制剂、TROP2 ADC等差异化管线,这种“壮士断腕”的果断值得我们学习。
结语
TIGIT靶点的集体溃败,或许正是肿瘤免疫疗法走向理性的转折点。在这场耗资数百亿美元的全球实验中,双抗、细胞疗法、表观遗传调控等新武器的出现,正在重写游戏规则。而TIGIT的故事也远未终结,它可能不会成为下一个PD-1,但在某些特定场景下,或许仍是拼图中不可或缺的一块。
参考资料:
[1]百济神州公告
[2]Novartis retreats from TIGIT, handing $300M candidate back to BeiGene.
[3]Nurix Licenses a Drug Discovery Program to Sanofi Targeting a Novel Transcription Factor for Autoimmune Diseases. Retrieved April 3, 2025



合作咨询
![]() 肖女士
肖女士
![]() 021-33392297
021-33392297
![]() Kelly.Xiao@imsinoexpo.com
Kelly.Xiao@imsinoexpo.com
 2006-2025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版权所有(保留一切权利)
沪ICP备05034851号-57
2006-2025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版权所有(保留一切权利)
沪ICP备05034851号-57